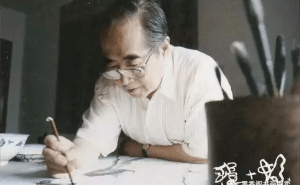在一个寻常的周末,一位热爱生活的作家决定采取行动,挽救几条即将成为他人盘中餐的鱼儿。他前往楼下池塘,从一对正在捞鱼的夫妇那里讨来了三条“鲢片子”,当地人又称其为“白条儿”。这些鱼儿幸运地被救下,被带回了作家的家中,安置在浴缸中,成为了他新的“室友”。作家笑称,这些鱼儿之所以“不怕死”,是因为他对它们的生死负有责任,毕竟,是他从“虎口”中将它们救下的。
为了驱散上周鱼缸遭遇“灭顶之灾”的阴霾,作家选择练习隋朝和尚智永的《千字文》字帖。智永与他的兄弟均出家为僧,据传他书写的《千字文》多达800余份,分赠予各地禅院。作家在提及《千字文》时,还分享了自己在一个多月前的科技大学外语学院“日语语言研究沙龙”上的经历,连日本老师也对其有所了解。他透露,从一位专门为他收集字帖的朋友那里购得的60卷《中国书法大全》中,找到了《千字文》的日文译本,译本精彩绝伦,将原本密集纠结的汉字文意,以日文片假名的方式舒展开来,使之仿佛成为了一部史诗般的“大文章”。

智永和尚的《千字文》字迹圆润、柔和,楷书与草书并存,使得书写者在楷书疲惫时,可转而练习草书。作家自中学起便熟悉日文片假名的写法,因此,他在摹写大字草书时游刃有余,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他认为,日文假名和汉字草书之间,存在着跨越千年的文脉联系,被借走的,如今又以另一种形式回归。他期待着,日本人也能有同样的认识。
周末的夜晚,作家前往中山音乐堂,聆听了一场由黄亚蒙带来的钢琴独奏会,中场解说由作家钟阿城担任。这是作家首次聆听钟阿城讲解西洋乐。阿城引经据典,提到《尚书》中的“歌咏言、诗言志”,并指出贵族无需“志”,因为生来便拥有一切,而“志”则是为骑士们准备的,因此贝多芬的曲目便属于后者。黄亚蒙后半场演奏的“迪亚贝里变奏曲”却让作家感到有些乏味,他认为贝多芬在这首作品中没有找到好的旋律,50分钟的演奏更像是“机械炫技”,未能达到“言志”和鼓舞人心的效果。作家对钟阿城的才华表示羡慕,认为他虽作品不多,却名声大噪。
音乐会之外,作家还享受了两个额外的“节目”:一是“听戏”,二是“看景”。中山音乐堂外的古松树上悬挂着的大月亮,成为了作家眼中的美景。中场休息和音乐会结束后回家的路上,他都欣赏到了这轮明月。尽管近年来对面的“国家大剧院”吸引了中山音乐堂的不少一流曲目,但这里的月色依旧迷人。
同一天,作家还参与了北京语言大学的本科答辩,久违地坐在了“评审席”上,感到十分得意。在答辩过程中,一位女生在陈述时滔滔不绝,但当被提问时,却仿佛刚刚听过贝多芬的钢琴曲,精神恍惚。尽管评委们一再提示,她仍一言不发,只是瞪大眼睛看着评委们,仿佛在等待他们回答问题。答辩结束后,一位女学生在楼道里哭着追骂一位女老师,抱怨自己已经第三次答辩,每次都要交750元费用,而这张文凭对她找工作至关重要,老师为何还要为难她。这一幕让作家深感担忧,生怕再发生意外。